多重身份的重叠使定义蔡朝阳成为一件难事。两年前,他离开了学校变成了自由职业者,但教育始终是他工作的核心.
此次,蔡朝阳老师作为第九期山乡教师成长计划的导师,将于11月与各位老师相聚在杭州良渚那个美丽的地方,共同探讨教育方面的问题。
为此,小编特意为大家介绍一下蔡朝阳老师,告诉大家,阿啃到底是谁?
文/羽戈
我喜欢阿啃这个名字更甚于其本尊蔡朝阳。这里并无大道理可讲,纯是个人兴味使然。唤作阿啃,备感亲切;称其蔡朝阳,客气之外,不免有点疏远。如果穷根究底,追问亲疏背后潜伏的意识,那我只能说:阿啃是一个吃货的名字,正对我的胃口。
事实上,阿啃远远称不上吃货,未免辜负了这个好名字。我与他共餐不下十次,发现他对食物并不怎么讲究,大抵是哪道菜端上来,便吃哪一道,距离他最近,便多夹两筷子。饭桌、以及茶桌、酒桌之上,他的快乐不在吃喝,而在说话,滔滔不绝,逸兴横飞。也许正因此,身为吃货的我,非常喜欢和他一起吃饭。他负责说话,我负责吃喝,大快朵颐之同时,还有一个名嘴谈笑助兴,实在是无与伦比的乐事。
阿啃不仅擅长说话,而且擅长与各种人说话,最关键的是,他擅长同时与各种人说话。这岂止一心二用呢,简直要五用、十用,相当于一位棋圣同时与五人、十人对弈,所考验的不仅是口才,还包括智商与反应力,以及风度。黄晓丹写过这一幕:阿啃的饭桌之上,充满各色人等,如编辑、教师、官员,当然从不缺闺蜜,普通话、绍兴话、诸暨话纷飞,“朝阳”、“蔡老师”、“阿啃”共鸣,对此,“阿老师谈笑风生,完全没有应接不暇的意思”。更令人钦佩的是,阿啃的风度,能让“桌上的每个人都觉得他说的话,阿啃听到了”。
阿啃笑迎八方客的背后,则是一腔赤诚。不论与成人说话,还是与孩子说话,不论与学者说话,还是与白丁说话,他一视同仁,从不敷衍。他曾经率领一个游学班来宁波,同行的司机是一位满面风霜之色的中年人,看起来读书不多,听我们横议国事,纵论江湖,直打呵欠,唯有阿啃能与之相谈甚欢。此刻我才亲见了黄晓丹描写的情形:阿啃和司机说绍兴话,和我们说普通话,和司机谈乡土,和我们谈思想,偶尔还和在旁边玩耍的儿子谈两句游戏与宠物,自由切换,从容不迫。他的真诚,连桌上的花生米和红烧肉都感动不已。
如黄晓丹写道:“我常常听到别人说,去了绍兴,和阿啃谈了什么什么问题。或者看到别人在文章里记忆某年某月与阿啃的某次谈话,使他的某个想法清晰了、确信了、得到印证了。我总是想,那八成又是去宣教了一番并吃了阿啃一顿。”江湖传言,现在去古城绍兴,沈园可以不游,鲁迅故居可以不拜,新青年书店(阿啃是股东之一)却必须一逛,阿啃老师必须一见。见到阿啃,以其土豪的身家与好客的习惯,必定会请你吃饱喝足,倘性情相投,还能享受一场精神盛宴。当朝拜者趋之若鹜,阿啃声名日显,是以有闲人总结:“为人不识蔡朝阳,便称英雄也白忙。”

我写这些细节,用意不在赞颂阿啃的情商与交际力,以及他对朋友“柔如流水,温如春光”的深情厚谊,而是试图提供一个直观的镜像,让不大了解阿啃的朋友明确两点:第一,阿啃有一种能力,使他周旋于各色朋友之间,令每个人如沐春风,甘之若饴,同时使他周旋于各色身份之间,周旋于工作与生活、思想与现实、理论与践履之间,游刃有余,进退裕如;第二,阿啃之于绍兴的意义,恰如绍兴之于阿啃的意义,他之所以能成为绍兴的一张名片,正源自他对绍兴的爱与奉献。
阿啃的身份之多,一度令我眼花缭乱。他曾经的职业是中学语文教师,曾通过民主竞选,担任学校的总务处副主任,主管基建;此外,他还是书店老板、假日学校的创办人与文化沙龙的组织者;文艺中年;资深奶爸……还是那句话,在他身上,这些身份体现的不是冲突,而是和谐,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向:公民。
如果要在二十世纪中国寻觅一个公民代表,我以为首推胡适,如果要在我身边寻觅一个公民代表,我以为首推阿啃。他几乎具备了公民的所有德行:自由、独立、理性、渐进、多元、宽容……
阿啃的公民转型,至少可以归结出五条线索,如从文学到政治,从激情到理性,从批判到建设,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等,我最感兴趣的一条,则是从鲁迅到胡适。阿啃生在了鲁迅的故乡,饱读鲁迅作品:他曾在绍兴的深夜读《坟》,读《野草》,读《南腔北调集》,读到一种抑郁从纸上泛起,从他心底泛起;他还写过许多关于鲁迅的文章,那篇《在鲁迅路口》,一度令我击节不止。然而,倘阅读《但得爱书人似我》,你会发觉,他越来越接近胡适,他的文章,从表达到说理,深具胡适遗风。其实,据我观察,他并未系统读过胡适的著作。对此,我的理解是:胡适并未远去,他就站在那里,每一个有志成为公民的中国人,都会不由自主,甚至不知不觉走向他、抵达他。阿啃便是一个生动的案例。

除了我总结的“从鲁迅到胡适”,阿啃的公民转型以及所表现的公民意识,还有三点特质,说是特质,实则与常识无异,只是在常识如此稀缺的当下,不免被视为特出。
第一,他拥有一个整全、自足的世界,这背后的决定因素,则是知行合一。要知道在吾国,教师尤其是文科教师的分裂,也许并不亚于官员。在阿啃身上,你却难以找出一丝分裂的伤痕。我不敢确证,他怎么想,就怎么说,却足可断言,他怎么说,就怎么做。譬如他主张自由教育,便推而行之,他的课堂,充满了自由及平等、开放的气息。他形容教师与学生的关系,不愿使用“医治”,而是“唤醒”,这两个词语的差异,端在于对自由的呵护。他给学生放映《死亡诗社》和《肖申克的救赎》,“这两部电影所表达的那种对自由可贵执著的追寻,一旦拥有,谁也不能夺走”。他不许学生喊他“船长”(有些教师则无比享受这一称谓),因为他的自我定位,不是《死亡诗社》里的基廷船长,而是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的安迪,他自称花了16年时间,来挖掘通往自由思想的道路”。这句话出自他在《一席》的演讲,演讲标题即“以自由看待教育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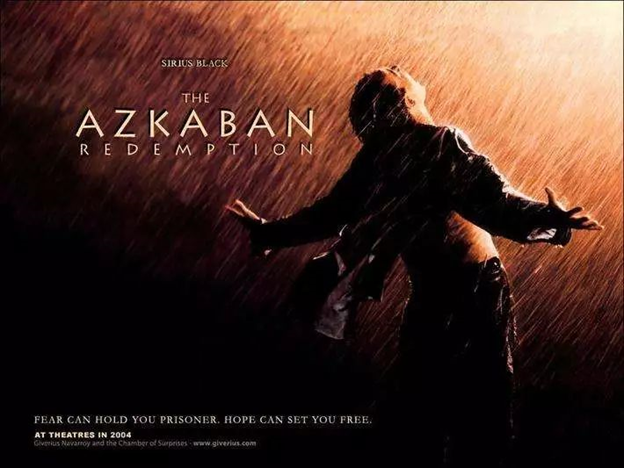
第二,阿啃热衷于“参与构成本地精神生活”。2009年夏天,阿啃到贵州遵义游历,偶入西西弗书店,在店中看到“参与构成本地精神生活”一语,若有所悟。他的公民生活,大抵分作两块,一块属于教师之职责,“我尽力让孩子们懂得自由为何物”;还有一块,则是以开书店、办讲座等方式,建构绍兴的公共生活:“我更希望以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的身份,为我所处的小城市增添一点文化气息。这完全建立在我对这个城市的爱之上。”
第三,他是一个快乐的反抗者。阿啃直言他不喜欢悲怆,他讨厌悲壮。譬如呼吁“救救孩子”的鲁迅,号召成年人“背着因袭的重担,肩住了黑暗的闸门”,历来为反抗者所挚爱。阿啃觉得,这太悲壮,太沉重,自由教育,无须如此。在他眼里,所谓“黑暗的闸门”,就是作业多不多,限制多不多。这一解释,便从黑暗回归光明,从悲情回归日常,令家长和孩子都如释重负。
不是说反抗者不能悲壮,而是,我揣摩阿啃的意思,假如能快乐反抗,何必悲壮呢?假如能扮演好兵帅克,何必佯装愁容骑士呢?假如能用微笑消解现实的坚冰,何必一脸苦闷呢?假如能像布拉格人那样,“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最后一击不是一刀,而是一个笑话”,岂非更好?
阿啃说他是“一个很浅薄的乐观主义者”,我想起胡适自称“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”。不知他们的乐观基于什么:人性、历史还是上帝。不过,对公民而言,他们建构公民社会的姿态与方式,决定了他们必须乐观。所谓姿态与方式,最经典的表达,就是日拱一卒,得寸进寸,就是“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”:胡适为中国科学社所撰的这句歌词,要义不仅在“一寸”,还在“欢喜”。
阿啃不是完人,我更无意把他塑造为完人。所以最后必须说说他喝酒的故事。这厮酒量深不可测,与我们一桌吃饭,却常常只喝可乐,自嘲“可乐党党魁”,无论谁来劝酒,怎么劝酒,他都坚贞不屈,不为所动。其理由无非是要开车,要带儿子,抑或陪闺蜜爬山……我们不耐聒噪,遂把他抛在一边,自行欢饮。待喝到醉眼朦胧,摇摇欲坠,阿啃忽然站起,拍桌喝道:我敬诸位兄弟三杯!我们大惊失色,不由疑问:你不是还要开车吗?阿啃道:不开了,豁出去了,陪兄弟们尽兴要紧,休得啰嗦,喝酒喝酒!此刻,我努力撑起沉重的眼皮,瞥向阿啃,昏昏灯火之下,他的身影愈发高大了。






